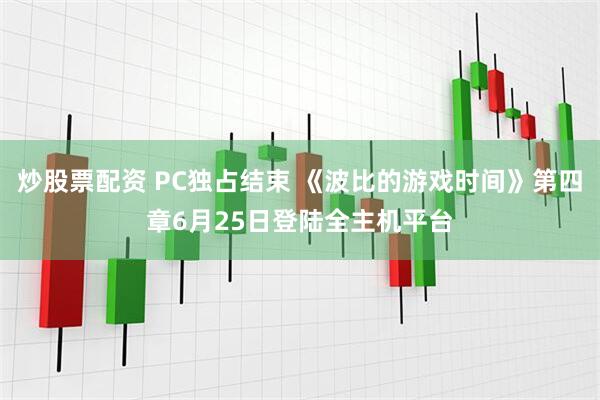最近,珊姐姐来到普宁洪阳的普宁学宫参观时(有兴趣了解详情的朋友,可以翻阅前面文章《隐藏在普宁“小众”古建,游客:比“粤东古建筑明珠”更原汁原味》),在参观普宁学宫时炒股票配资,珊姐姐在大成门看到了一幅图片介绍,瞬间好奇心被点燃。图片显示,普宁学宫居然还保存着一座“魏忠贤的生祠”,旁边还有一座石像。这不禁让人疑惑:这真的是魏忠贤的生祠吗?石像难道就是魏忠贤本人?


在古代中国,祠堂是极为神圣的地方。一般来说,祠堂是为逝去的先贤建立的,但也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给活着的人建祠堂,这种祠堂有个专门的称呼——“生祠”。说起生祠,最广为人知的当属明朝大太监魏忠贤的生祠。魏忠贤出生于1568年,是北直隶肃宁(今河北沧州肃宁县)人,自宫后改名叫李进忠,后来出任秉笔太监,又改回原姓,还得到皇帝赐名魏忠贤。天启六年,浙江巡抚潘汝祯以杭州织造机工的名义,给魏忠贤修建了一座生祠。当时魏忠贤权势滔天,很多人或是阿谀奉承,或是畏惧他的势力,在全国范围内纷纷为他建造生祠。不过,崇祯帝即位后,魏忠贤的阉党势力被扫除,他本人也自杀身亡,各地为他建造的生祠、牌坊、碑刻等都被下令拆除。那普宁学宫的这座“生祠”又是怎么回事呢?

按照普宁学宫的指引,珊姐姐在学宫东路儒学门后找到了一座石亭。这座石亭已经过修复,从造型和样貌来看,有着明朝至清中早期的风格,可惜的是,亭子中的碑已经不知所踪。石亭中有一座石像特别引人注目:这尊石像由青石雕刻而成,有1米多高,整体呈扁平状。石像只有正面经过雕琢,人物头戴文官帽,面部神情庄严,只是鼻子已经损毁,身穿圆领袍,还配有腰带,双手藏在袖子里,相交放在腹前的膝盖上,是坐像的造型。而石像的其他部分,要么是原石的样子,要么只是简单地凿了几下,背面凹凸不平,右下角甚至还保留着开石时的凿孔。从整体情况判断,这尊石像原本应该是嵌在所祀地点的后主墙上,只露出正面的半身,供人们瞻仰膜拜。

参观完普宁学宫后,珊姐姐就想:凭一座亭及一石像,就认为是监魏忠贤的生祠?好奇的我还曾向普宁当地的朋友请教,朋友们说,听长辈讲,这座石像是“石状元”。以前,民众到学宫祭拜孔子的时候,都会先在这里拜拜“石状元”,希望家里的孩子读书聪明,能够文运昌盛。虽然当地人都称石像为“石状元”,但由于不清楚这个“石状元”到底是谁。

参观完普宁学宫回到广州后,珊姐姐查阅了大量资料,之所以认为是魏忠贤生祠,是有人看到石像穿着文官服饰,而且面部光滑没有胡须,尤其是面滑无须这一点,再结合明末的历史事件,就把石像传成了明天启年间的大太监“九千岁”魏忠贤,而石像所在的石亭,也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魏忠贤的生祠。但这种说法真的有依据吗?

我们再查阅当年的历史:明天启皇帝驾崩后,崇祯皇帝继位,魏忠贤的“造神运动”也随之终结。崇祯皇帝下旨,不论魏忠贤的生祠在京城还是外地,不管是已经建好的还是正在建造的,都要全部拆毁变卖,所得款项用来资助边防;建在国学里的生祠更是不能容忍,要立刻拆毁,不准留存或改作他用。奢华又荒唐的魏忠贤生祠被定性为“逆祠”,全部被毁掉。

从这些记载来看,魏忠贤生祠与配祀孔子的事件发生在明天启六年闰六月到七年八月之间,前后不过一年三个月。很难想象,这么荒诞的政策能从北京城传到地处南方省尾国角的普宁这样一个小县。更何况,提出让魏忠贤配祀孔子是在天启七年四月,距离魏忠贤集团覆灭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了。而且,用来讨好权倾天下的魏忠贤的生祠,真的会只用一座石亭来敷衍了事吗?魏忠贤的塑像又怎会如此粗糙地立在亭中,还守在门口呢?

为了揭开真相,珊姐姐深入研究,最终在清乾隆、光绪两版《普宁县志》中找到了线索。清光绪十四年《普宁县志稿》艺文一节中,知县张璿所作的《重修文昌宫碑记》,以及卷十中知县罗秉琦所作的《新建文昌阁分司公馆碑记》,都为解开谜团提供了关键信息:原来,普宁学宫内的“石状元”,其实是明崇祯年间建在洪阳城外昆头山文昌宫内的文昌帝君像。后来文昌宫遭遇火灾被焚毁,这座神像才被移到城内学宫大成门左侧暂时安置。再结合普宁学宫的历史沿革和其他资料推测,清初顺治年间,普宁学宫先后两次遭到战乱破坏,或许就在那段时间,文昌帝君的石像被湮没在水土之中。过了两三个世纪,可能是在挖井或者清理池塘的时候,石像又被发现并重新扶起,但此时它已经变成了无人知晓的“石状元”,一直留存到现在。
至此,普宁学宫“魏忠贤生祠及石像”的谜团终于被解开。一段因历史久远、信息缺失而产生的误传,在经过深入研究和考证后,还原了本来的面目。这不仅让我们对普宁学宫的历史有了更准确的认识,也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研究的魅力和重要性。
美林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